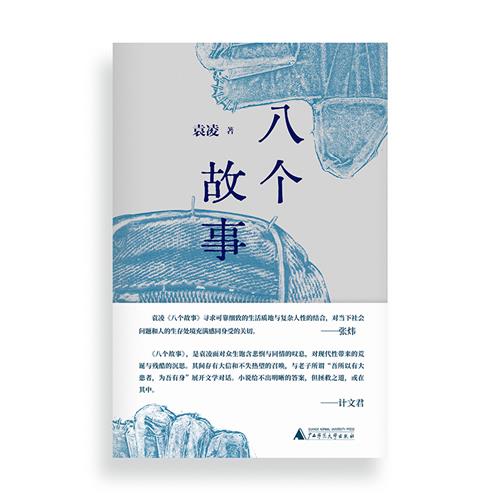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1-01
定 价:58.00
作 者:袁凌 著
责 编:吴义红
图书分类: 经典阅读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文学·小说
开本: 32
字数: 170 (千字)
页数: 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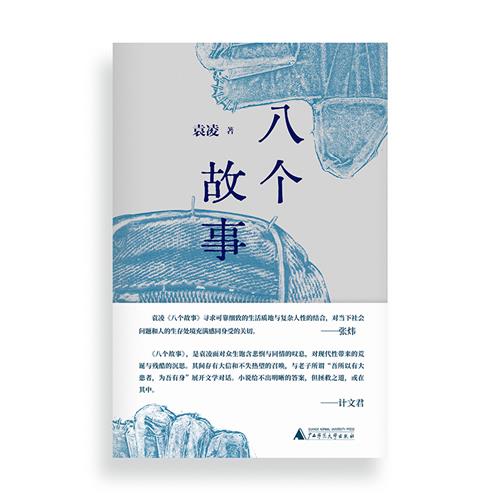
袁凌《八个故事》共包括八篇作品,篇目有《大杂院子弟》《墨菲定律》《彩色骨灰》《亲爱的皮囊》《鸟神》《此人纯属虚构》《山》《聊天》。作品题材与行文风格统一,着眼于通过对平凡人市井生活和繁杂琐碎的家长里短的描写,刻画当下都市漂泊者及边缘者等普通人的内在心境和生存状态,探索人与城市,异乡与故土,人性与现实的分裂、张力与平衡,具有很强的冲击感,使忙碌奔波于生活中的人们能在本书中找到心灵的共鸣和情感的归宿。
袁凌,生于陕西平利县,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历任《凤凰周刊》主笔、《Lens》主笔、《财经》记者等职,曾任新媒体“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曾获“2015 腾讯年度非虚构作家”,2017 新京报·腾讯“年度致敬作家”,单向街“2019 年度青年作家”。入选三届收获文学排行榜非虚构类前三、两届豆瓣年度作品、两届新浪“十大好书”、两届华文“十大好书”、两届南都“十大好书”、凤凰网年度好书、单向街年度作品等,另曾提名或入围首届吕梁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新京报十大好书、新周刊年度好书、2020 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散文家等多种奖项。
出版作品有《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世界》《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寂静的孩子》《生死课》《记忆之城》《汉水的身世》等;在《收获》《人民文学》《花城》《十月》《中国作家》《作家》《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诗歌等数十万字,曾在《上海文学》《延河》开设过非虚构和小说专栏。
大杂院子弟/001
墨菲定律/053
彩色骨灰/117
亲爱的皮囊/145
鸟神/191
此人纯属虚构/205
山/235
聊天/263
序
本集收入我近年所写小说。
大疫之年,迁居长安,往返京陕。屡遭隔离,常怀忧煎。世人困境,深有所感,背井离乡,孤独内卷,省漂北漂,身心不安。身边亲友,路上行人,有忽然辞世,有返乡躺平,有朝九晚九,有抑郁沉绵,有终身不婚,有亲情离间。其名自由,其实自受。其名福报,其实榨干。负此皮囊,奔波世间,一床一饭,已甚艰难。加之情感需求,精神负担,头顶星空,脚下泥潭。众生皆苦,岂为虚言。爱欲交织,人性本原。
偶成篇什,集为斯编。立此存照,凉热人间。
疫后癸卯春月于燕京十里堡
袁凌《八个故事》寻求可靠细致的生活质地与复杂人性的结合,对当下社会问题和人的生存处境充满感同身受的关切。
——张炜
《八个故事》,是袁凌面对众生饱含悲悯与同情的叹息,对现代性带来的荒诞与残酷的沉思。其间存有大信和不失热望的召唤,与老子所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展开文学对话。小说给不出明晰的答案,但拯救之道,或在其中。
——计文君
袁凌由“非虚构”而“虚构”,他笔下的小人物真实可感,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颠沛流离,却始终保持着生命的热情和人性的温暖。《八个故事》是一幅时代生活的肖像图。
——杨庆祥
我不大愿意将袁凌视为一个“异类”,但他显然特异,夸张点儿说: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平衡了当下小说现场天平的另一极。
——弋舟
袁凌《八个故事》带有很强的纪实性,从故事情节到人名、地名,都给读者非虚构的直觉。各篇故事基调、题材具有同一性,都是直面北漂在社会底层小人物挣扎的酸甜苦辣,这种平凡人的市井生活,和老舍笔下的老北京既有相似之处,更有新时代的特点。通过刻画当下都市漂泊者复杂的心态和城乡杂处的生活状态,揭示出这些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困顿迷茫的窘境。
墨菲定律
一
在与一苇和母亲柯凡的关系当中,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心理师,父亲的老同学,叔叔,朋友,还是她叫的哥哥,或别的。
和很多早期的同行一样,我也是半路出家的。从鹤岗辞掉厂部宣传科的工作来到北京之后,我还做了不少年头跟煤有瓜葛的生意,譬如劳保用品、小型机械啥的,都是跟人合伙,拿小头。后来煤矿关的越来越多,慢慢地终究做不下去了,以前赚的些许都赔了进去,一直没在北京扎下根来,家庭也破裂了。有一段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晚上睡不着觉,从单人床上起身成了登长白山一样的事。有一次这样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之后,身体轻飘得像张纸,肚子却咕咕雷鸣起来,我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病急乱投医,去看了两次心理咨询师,当时还是个新鲜东西,觉得效果也不是很大。后来忽然想到,现在心理出问题的人多,这倒是个有前途的行当。好在大学学的是中文,又爱看些心理小说,转起方向来倒不算是太匪夷所思。那时候国家还有二级心理师考试,我用两年考了个证书,在北京三环之外租了个稍微大点的房间兼作住处和工作室,就算转行开张了。
十多年下来,我没能靠这行在北京买房子扎根,只是挣一口饭吃。心理学的理论一直在变,女客户是大多数,往往喜欢挑女心理师,还兴起能量疗愈的一派,桌上摆个水晶球,一手覆在球上,随便打量几眼客户,就算是接通了能量场,看透了来人的前世今生。这总让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跳大神。
我像是起了个大早赶上晚集,常常感觉过气了半截。近两年,我从事务所里出来单干,除了坐等客人上门咨询,我也学习别人建了一个微信群读书会,通过带领人一起读某一本书,一面收点会费,一面培养粉丝。一苇妈妈加入那段时间,我们在读的是《墨菲定律》。
起先我没在意柯凡的加入,她是群里两个鹤岗老乡拉进来的。不怎么发言,只是静静地潜水。直到半年多以后,到了要交下一季会费的时候,我逐个清点群里的成员,到了她的名字,默默打算将本来不算长的名单划去一格了。没料到柯凡不但续了费,还提出找我做一次心理咨询。
因为是第一次,我估摸着报了一个不高不低的价位,约好在我的住处兼工作室见面。这时因为北京的房租涨价,我已经又往外迁了两环,到天通苑二区地铁步行十来分钟的地方租房了。顾客下了地铁,走到稍微不耐烦的时候,也就到了。
柯凡出现的时候我有些吃惊,看上去像在哪里见过。她面容白皙但是皱纹偏多,约略看得出年轻时的清秀,个子不低,穿一件浅色外套,里面是恒源祥羊毛衫。头发看得出用心捯饬过,却被北京无处不在的风吹乱了,马尾上还落了一粒杨絮,远看像是鸡毛。我看着她心想,也许我们在鹤岗的公交站牌下一起等过车,或者共同在一个菜摊前停留,仅此而已。但当初她的面容一定是有些出挑,给我留下了印象。
咨询进行得有些费事。她叙述起来语无伦次,总是陷在自己的某个思路里,看不到同一件事情可以做完全别样的解释,每当这时候,我面前总像并非一个人,而是一只落网的飞虫,或者动物园铁笼中兜圈子的熊。我自己的心情也变得郁闷起来,因为在客人身上看到了自己。身为咨询师又不能太干预,只能顺着她说下去,实在不行的时候才表现得不经意地提醒一下,这主要是为了时间。两小时的咨询收费九百块,虽然我的时间并非如此紧缺,却也不能随意延长。
她叙述的线索在眼下和过往之间缠绕,好久之后我总算理出了一点头绪。她早年在鹤岗结过一次婚,生下了女儿,没几年就由于男方的大男子主义和养小三离婚了。以后她带着女儿过,没有再成家,甚至没有再找过男人。女儿考上大学后,她跟着亲戚来到北京,做医疗销售代表和物业管理之类的工作,把女儿一苇送去了日本留学。女儿半年前从日本回来,和她的关系出现了很大问题,像是变了一个人。
听她说着以往的经历,我又产生了某种熟悉感。似乎她生活中的哪个线头,和我已经在那个小城抛离多年的记忆某处是连缀在一起的。她是从小城考到沈阳去的大学生,在那一代人里面属于拔尖的,毕业后分配回到鹤岗,和铁矿上的一个人结婚。夫妻俩一起下海做生意,发了家,由于丈夫出轨和用度上的毫无节制,两人离婚,生意也破产了。也许是因为在东北有太多这样的情节,一遍遍地上演,没有谁是纯粹置身事外的看客。
丈夫早已不再联络,她现在最头疼的是女儿的事情。女儿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乖巧听话的别家孩子,也顺利地考上了省城一座不错的大学。去日本留学期间,母女定期联系,也没有特别表现出什么异样。回国之后,一苇却表现得事事忤逆,从找工作到交男友、日常生活习惯,你叫她往东,她一定往西,找关系让她去面试,她故意穿成吊儿郎当的装束,用开玩笑的语气回答问题,把面试搞砸了,回来还显得很开心,像是很有面子一样。进了一家外贸公司,没两个月就出来了,说是不想在日本人的公司干。自己说要找别的工作,却又不见下文。外出时候不打招呼,问她见什么朋友不回答,好的坏的一概不知。
在家的时候,习惯把房间门关起来,一整天不出门地刷手机,只有吃饭的时候会打照面。偶尔进去一看,乱得不像个女孩子的房间了,还有一种昏昏沉沉的气味,一点不像是年轻人该有的朝气。多问她两句,就吵起来。柯凡说,她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说到这里,她似乎会像很多女人一样流泪,准备去拎包里掏餐巾纸了,但终究没有流出泪来,只是眼圈红了。看起来她终究是个要强的女人。
我只能按通常的理论做一些解释,知道对她的问题其实是隔靴搔痒。我提醒柯凡注意一苇从小经历了父母离婚,在单亲家庭长大这一事实,这类孩子的心理相比完整家庭的孩子,不论如何都有更敏感的地方。作为母亲,需要和女儿加强沟通,多从一苇的角度想一想,毕竟她已经成年了。
柯凡起身收拾拎包,一边礼貌地点点头,我不知道对我的话她听进去了多少,不过看上去她到底放松了一些,还转脸打量了我一眼。这张脸我到底在哪里见过呢?正打算送柯凡出门的时候,她停下来问我,你是不是周北方的同学。我有些意外地回答是的。她点点头说,周北方是我的前夫。
她这么一说,我脑子里那些散落的线条算是搭上了。周北方确实是我的同学,但他比我大上四五岁,高中时留级和我到了一个班里。他没有考上大学,复读了一年没有改观,顶班进了矿务局下属的机械厂。他是那种外形轮廓很扎眼的男生,因为大了几岁,在班级也很有大哥范,虽然不受老师重视,却总有几个小弟跟随左右,那时候就经常下馆子吹扎啤。他下海之后,喝酒成就了他的生意,曾经显赫一时,在同学圈中召集每年度的饭局,饭局上他的酒量永远首屈一指,比我们这几个上了大学进单位拿死工资,喝不敢喝赌不敢赌的人要潇洒得多。并且他还找了一位女大学生做老婆,照片上柯凡的容貌更是引人羡慕。
但喝酒和赌博最终也毁了他,听说他落到妻离子散还坐了几年牢,坐牢期间结了婚的小三也离开了。最近几年他再度出现在同学微信群里,开头说是再度创业成功,不时显摆几张坐宝马赴酒局的照片,后来却开始找同学借钱,不过到现在并未借到我头上,大约他也觉得干个心理咨询什么的实在没有多大油水,不过我还是有几分终究会被他点名的忐忑。
我没有见过柯凡,仅仅是看到过周北方手机里展示给大家的照片。但柯凡说,她早就从一个老乡处知道我是周北方的同学,这也是她愿意加入微信学习群,和眼下来找我咨询的原因。
我想告诉她,这种熟人间的心理咨询其实是不合适的,因为咨询师会有代入感,又牵涉到很多隐私。不过我和周北方上学期间并不亲密,除了同学圈也没有更深的交集,长年北漂,这方面的忌讳也就少了一些。倒是有点担心,我这间一半像是住处的工作室给她留下了什么印象。
以后我们偶尔在微信上聊几句天,没太提到过去在鹤岗的事,她会就课程学习里的一些疑点单独问我。有几个群友也习惯像她这样,后来他们商量之后提出建议,在线上的读书讨论之外,再搞一个定期线下聚会,当面交流,参与者另外缴纳一笔会费。柯凡也参与了,虽然我知道她在物业的工资并不算高。
因为我的住处太过偏远,大家约定在雍和宫附近的一家星巴克定时聚会,那里平时人多,周末的上座率不高,我们的讨论不大会干扰到别人。聚会时大家各点自己的饮料,轮流帮我点一份,阅读的书目仍然是从《墨菲定律》开头,渐渐地大家习惯了坐下来先聊一下家常,再开始读书。柯凡往往是来得最早的一个,在角落里占好位置,就着有些昏黄的灯光读膝盖上摊开的书,偶尔会让我想起她的老大学生身份。
像加入线上读书会的经过一样,柯凡一开始仍然是最沉默的一个,似乎她额外交了钱的目的只是来这里点杯饮料坐下,当面倾听大家讲话。后来在拉家常之中她也渐渐会说上两句,但仍旧显得矜持。聚会结束后各自回家,多数人是走到雍和宫站分头搭地铁,我搭五号线回天通苑,柯凡和另两个人是转二号线,她的住处在上地附近,需要到西直门再转乘十三号线。
有一天在二号线地铁站台上,柯凡提出跟我一起去搭五号线,到立水桥再转乘十三号线。我觉得她这样比较绕,但没有说出来,一起上了晚上十点过了仍然显得拥挤的五号线地铁。
地铁上没有座位,我们站在过了惠新西街南口不再开启的车门一边。地铁过了惠新西街北口,开始钻出地面的时候,她背靠着车门问我,如何能让自己想到前夫时不再愤怒?
她说,自己现在看到女儿的一举一动,都会想到前夫,忍不住想骂人,吵架。一苇现在越来越像爸爸了,有时候她都觉得女儿是故意的,为了气她。
车窗外北京的灯火点缀在黑暗的背景中,在柯凡身后时而闪过,不足以照亮奥森公园到西山一带大片的黑暗。黑暗中浮现出了我的那位高中同窗的脸。在班上他经常是中心,而我只是个小不点儿,甚至可以说受到过他的欺负,当然对他来说可能是不经意的,就像人会不经意地伸手去按一下树皮上的一只昆虫。后来听说他的没落,心也会像风吹的水面,掠过一丝轻微的绉纹。
这样的联想其实是不专业的。确实我和柯凡在这时并不是在进行心理咨询,像是两个老友在聊天,她也没有因此付费,但她毕竟是我的忠实客户。我把心思收回来,问一苇和她爸感情好吗。
不好。小时候他也还算疼她,但没多久就闹离婚,他很少回家来,都是我抚养她。再后来,一苇不愿意见她爸,现在更是不愿意人提到她爸。
那你就不能说她像她爸了。你不能在她身上找她爸的影子,对她的伤害会很大。
但她行为举止就是像她爸。邋遢没个边儿,睡早床,到了快吃午饭时还不起床。屋里一股气味。说话特别难听,要不不理你,当你在屋顶下不存在。作息颠倒,半夜刷手机,有时候还跟人出去,很晚才回来,身上一股酒气,说是朋友,不知道是哪来的朋友。越看越像她爸,来气。小时候她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想告诉她,这是心理学上的投射机制,你是把对于丈夫的怨念投射到了女儿身上,这样你会怎么看她怎么像她爸。但说得这样直接并不合适。我只是告诉柯凡,人的心理是互动的,共同推动一件事情向前发展,你越看越像,她就会真的越来越像;你看着不像了,她可能就会越来越不像。这是我们正在学的墨菲定律。
柯凡认真地听着,没有回答。灯火和黑暗依旧交替在她的面容背后闪过。
车上变得空了一些,但我们都没有坐下来。柯凡换了个话头说,她觉得一苇大学学的是外语,又到日本留过学,最合适的就是到外贸公司,可是她就是不愿意,宁肯去找那些不靠谱的什么文化创业公司。她还是觉得,女儿在日本遇到了什么事。
车到立水桥的时候,她忘了下车,我提醒了她一下,她才忽然回过神来。“谢谢你免费听我吐槽,下次再见啊。”我说都是老乡没问题。她冲我微笑了一下,有些急促地跟在别人身后出了车门。
在天通苑下了地铁,正在过天桥的时候,我接到她的一条微信,说有机会的话,让一苇找你聊聊吧。我说可以,不过我估计她不大会愿意,现在她处于自我封闭期。
我沿着一区南边的街道走回家去,这条街道现在变得安静,前两年靠近地铁站排开了半条街的烤面筋、炒河粉和小螺蛳摊子都被清理掉了,再也没有那种闹哄哄的喧嚣,想到这件事情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遗憾。小区铁栅栏有一处铁条被人掰弯了,辟出一个可以进入的洞,比走到小区入口进去再绕回来要省一些路,我像别的赶时间的上班族一样钻进这个洞,越过绿植区走向自己租住的楼房。这几年绿植区栽了不少桑树,暗中闻到一种像是酒酢的气息,忽然想到是桑葚成熟了。我也曾不顾打过农药的警示摘下一捧来吃,享用一点酸酸甜甜的南方滋味,但今晚有些心不在焉。
柯凡和她女儿一苇的事情,不知为何占据了我一部分的心理空间,我想到她和周北方那种难解难分的关系,想到可能会见面的一苇,我老同学的女儿;我感到某种好奇,这超出了一个咨询师应该有的心理活动。
二
一苇申请加我的微信,看她的昵称是“胡不归”,加上以后她问我,知道这三个字的意思吗,我说知道。式微式微胡不归,混得不好干吗不回去。一苇看似对我的解释很满意,哈哈笑起来。交谈变得意外的轻松,我们约定在天通苑华联广场一家咖啡馆见面。
这里离我的住处不算很远,我偶尔会来吃一顿快餐,再骑上二十分钟共享单车回家。那天我扫了一辆小黄车骑到华联广场,外面新开张了一个露天儿童乐园,一些家长正在带领小孩子玩西瓜大作战,旁边矗立的网兜城堡上也有不少孩子在攀上爬下。看来天通苑除了晚上过夜的人多,周末的白天也逐渐热闹起来了。这意味着很多北漂一族有了下一代。
忽然想到分手了多年的她,如今她大约也漂泊在这座过于广大的城市里,在北京拥有自己一套房子的愿望,或许实现了吧。我不是那个适合帮助她实现愿望的人,更谈不上和她繁衍下一代。她的孩子如今是不是也过了玩西瓜大作战的年纪,在哪座网兜城堡上爬上爬下呢?
走进Costa,一苇已经坐在那里,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很不相同。她的头发焗过油,不过褪掉了一些,颜色正好达不到鲜亮得反常的程度,又有几分亮眼。一身水红色的穿着显得时髦,深V敞口的衣领露出一抹乳沟,显得有一点过于性感,和她单薄的身板及年龄不大匹配,也引来咖啡馆里旁人的目光。她的脸上有一点微笑又捉摸不透的神情,近于某种媚态,却又像是很天真,让人把握不出她的心思。
她的饮料已经点过,我另外再给她点了一杯草莓奶昔,试着跟她聊起来,话题闪闪烁烁,不大敢去触碰有关父亲和日本的话题。她倒似乎经过审视,对我落落大方了起来,渐渐说到在鹤岗的一些往事。那个除了冬天的白和其他季节的黑几乎没有别的颜色的城市,她没有任何怀旧之情,小时候只记得家境不错,比起周围的人来都要好一些,后来有一天父母突然开始吵架,她脑子里面的第一个印象是父母站在客厅大茶几的两头,因为父亲经常带朋友来家里吞云吐雾小菜下酒,茶几做得特别的大,水晶的烟灰缸里总是摁满了烟蒂,那天烟灰缸不知怎么到了父亲手里,朝另一头的母亲挥舞着,随时会扔出去,一些积存的烟灰随风飘落,到了坐在沙发上的一苇眼睛里。一苇揉着眼睛却不敢哭,父亲口里吐出一连串骂娘的言辞,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茶几另一头的母亲只是冷冷地盯着他,声音不高不低地回上两句,却对父亲具有极大的杀伤力,让父亲更加暴跳如雷,最终却又彻底泄气,冲出家门一走了之。一苇的眼睛这时已经被烟灰扎得流了好多泪水,却不敢真正地哭,怕哭泣惹得母亲更不高兴。她明白在这场剧烈的冲突中,尽管父亲的声音更高,动作更吓人,得胜的却是母亲,父亲实际上一败涂地。一苇除了跟随母亲进退,没有任何办法。
后来一苇听母亲说父亲找了小三,跟着就是离婚。离婚之后,有段时间父亲给生活费,后来说没钱给了,但还偶尔打电话过来,要一苇去他那里玩,“直到妈妈让我去跟爸爸要房子”。
妈妈怎么会让你去要房子?
是啊,那次让我很恨她。一苇画过的眼角有点上挑起来说。
九岁那年一苇放暑假,爸爸让她过去玩一天。临走前妈妈特意嘱咐,爸爸现在不按时给生活费了,他住的房子当初说好是给你的,只是让他一时借住在那里。现在他跟那个女人结了婚,生了孩子,还住那房子,将来这房子就归了别人了。我打电话他总是不接,你去跟他开口要房子,这房子是你的。
到了父亲家里,并没有见到母亲口中那个小三女人。父亲陪着她出门去买蛋挞和棉花糖,去了天水湖公园划船,在大黄鸭船上她提了房子的事。
在划船的父亲脸色立刻就变了,一苇开始担心他会把她扔下水去,父亲只是沉默地把船划到了岸边,当天的游玩就此结束,父亲没有留她吃晚饭就送她上了公交。到家之后母亲问一苇有没有对父亲提房子的事,一苇说提了,但没说船上的事。
以后一苇常常想起父亲脸上像是瞬间戴上了面具的表情,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一苇大体上就明白了,几年间再没去过父亲家。到北京之后,听说父亲试图再次创业,因为诈骗罪坐牢了,到了十七岁那年,父亲从牢里出来了,母亲打听到那套房子没有被法院没收拍卖,又让一苇主动跟爸爸联系,“顺带提一下房子的事情”。
正在吃饭的一苇感到愤怒,把饭碗一摔,忽然间就跟妈妈吵起来了。
妈妈的脾气很暴烈。小时候她的要求很严格,如果有什么方面达不到,她会很严厉地责骂,有时候还会动手。和父亲吵了架之后,她的脾气会变得很差。离婚之后,她的脾气更糟了,一苇根本不敢有一点违背,这次不知怎么就爆发出来,连柯凡也一时愣住了。
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没办好,为什么要指使我?那个房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想要你自己去要,不要拿我当枪使!一苇一口气对母亲喊出了这些话,自己都被自己的勇气吓住了。她浑身颤抖起来,脸颊不由自主地收紧,等待着母亲暴怒的耳光落上来。
意外的是那次柯凡并没有动手打人,只是冲女儿嚷嚷,这本来就是你的房子,你看我们现在还是租房住,没个自己的地方。一苇说我一点儿都不想要什么房子。争吵含含糊糊地过去了,柯凡没再对女儿提起这件事,一苇也没有跟父亲联系过。柯凡并没有忘记那套已经变成了白菜价的房子,在穿过半个北京的五号线地铁上,她曾经两次对我提起来,只是没有说到过让女儿去索要的事情。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那套房子里,她曾经是真正的女主人。
这套鹤岗的房子对于一苇毫无意义,里面没有留下跟一苇有关的东西,除了一个铁臂阿童木玩偶,日本货,胸口会发光会呜呜叫,是爸爸有次去日本给一苇带回来的,这也是爸爸唯一的一次给一苇买玩具。这个阿童木一苇还玩了两年,直到和妈妈一起离开那套房子,一苇手里拿上了它,被妈妈夺下去扔在沙发上,说这是你爸爸买的,我们不要。出门的时候一苇最后看了屋里一眼,只见那个玩掉了漆的阿童木孤零零躺在沙发上。
一苇觉得哪里也不是自己的家。不管是有一套据说是登记在自己名字下的房子的鹤岗,还是和母亲多年租房住的北京,甚至中国,一苇都没有什么感觉,大学毕业之前,她根本不想在东北找工作,连北京也没兴趣,只想走得越远越好。
上中学时,一苇的学习很出色,在这方面没有违反母亲的要求,尽管经常会由于玩手机或者偷懒受到批评。她顺利地通过了高考,比柯凡的母校要高出一档。在大学里,一苇成绩不错,和同学们的关系也还算好。母亲满足了她去日本留学的愿望,到了日本之后,看起来日子也还顺心。但是回国后一切都变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聊天的后半段,我委婉地提出这个疑问,尽量避免让她感觉是她母亲让我来问的。一苇却很坦然地回答了,说是毕业前不久被性侵过。
当时她并没打算回国,想要在日本找机会实习,留下来。有一次去一个株式会社应聘,在一个特别偏远的工业区,会社在一幢近乎半废弃的大楼里,走进去时空无一人。她有些害怕,但还是坐电梯到了四楼,敲开了那家会社的门,里面只坐着一个相貌猥琐的男子,看起来像是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他假模假式地询问了一苇几句,很快就跟那些AV片里的情节一样,离开了桌子开始对一苇动手动脚,撕开了一苇的衣服和裙子。
一苇的力气很小,脑子里近乎一片空白,但和AV片里那些性侵实习生的场面不同的是,这个猥琐的男人阳痿,没能真的强奸一苇,但他的手指伸进一苇下体乱捅了一阵,一苇觉得特别疼痛,大喊大叫使劲挣扎,后来他可能觉得害怕和无趣了,放开了一苇,一苇赶紧逃出了办公室,不敢等电梯,一路从楼梯跌撞逃下去,离开了那个工业区。这件事发生之后,一苇就不打算留在日本了。
母亲旁敲侧击问过她好几回,最近两次甚至是逼问,一苇都没有回答。除了在日本时的舍友和个别朋友,我是知道这事的第三个人。还好身体没有留下后遗症,但她做过好多次还原这个场景的噩梦,这也是她一到日本那种株式会社里上班就受不了的原因。在那之前,她在日本还遭遇过尾随。就是那种电视上演的痴汉,头发乱糟糟的,穿花格子衬衣,等在她下课的地方,一路尾随她到住处外边,她吓得两腿都在抖,当时她住的地方在一片墓地前面,比较偏僻,事后赶紧搬了家。
但是现在,她又想再次回日本去,感觉自己还是挺喜欢那里的。但是柯凡说了,不可能再供她回日本,家里根本没有这笔钱。
柯凡跟我说过,回国以来女儿没挣钱,除了吃住在家里,还额外花了她两万块钱,她自己从物业公司离职,还要租房,已经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了。
假如在国内,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想找文化艺术方面的,一苇说。她不喜欢做生意那些事情,很枯燥。在日本,她喜欢那里的文化气息,自己也喜欢写点小文章,还画过一段速写,只是没坚持下去。回国之后,也没有那样自然的风光了。这段时间她认识了一些文化产业方面的朋友,她打算去试一试,如果能上班挣钱,就可以从家里搬出去,她实在不愿意和柯凡待在一块了。
聊天结束后,我送她上了滴滴快车,自己去坐地铁。她问我刚才也是坐地铁来的啊。我说是的,习惯了公共交通。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一苇轻笑了一下。
我跟你说的那件事,是信任你,你一定不要告诉柯凡。
钻进车门的时候,她回头来对我说。
一定。我说。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2024澳门2024免费原料网44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email protected]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